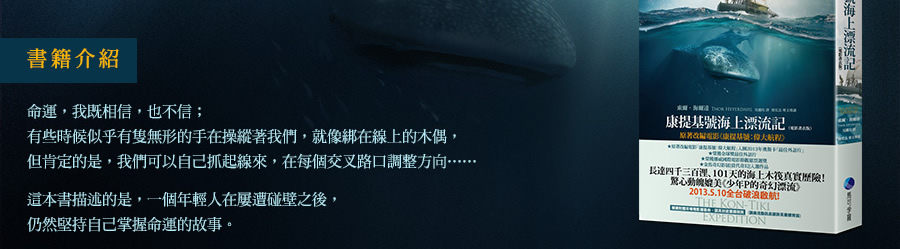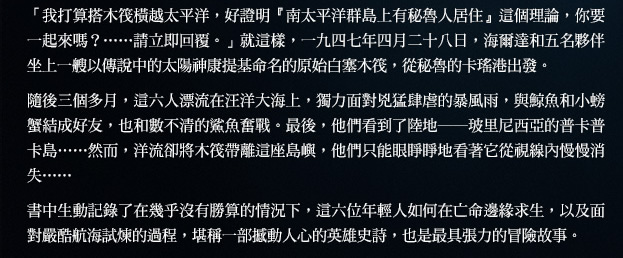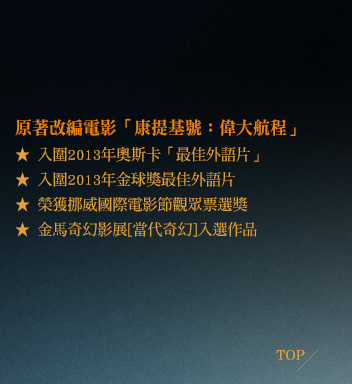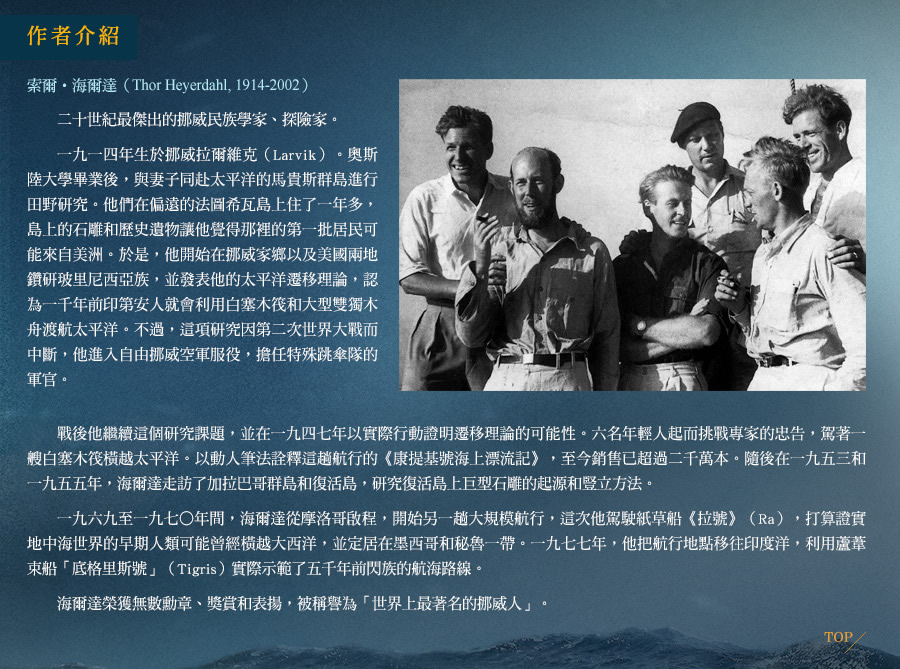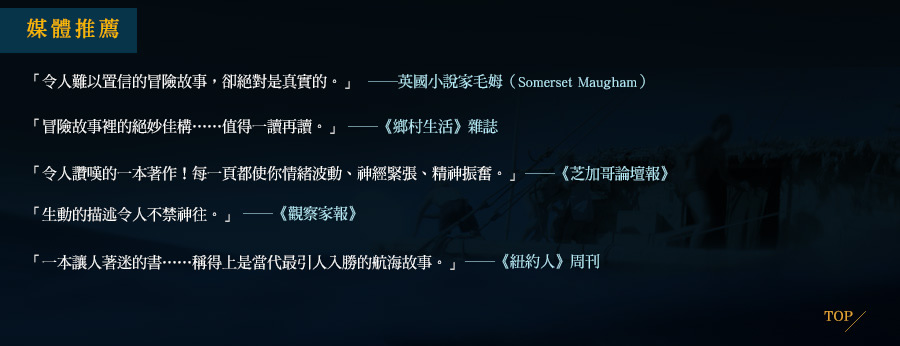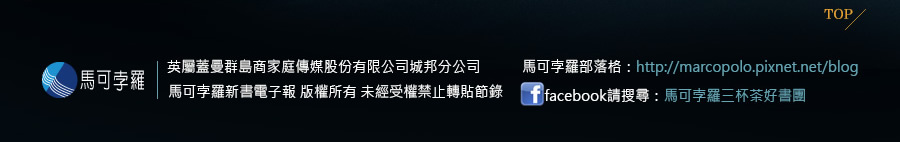還有太多事情要做,而且大部分的事都得同時完成,才能讓六個人、一艘木筏和其他貨物,在秘魯沿海的一個地方集合起來。而我們只有三個月的時間,又沒有阿拉丁神燈可以用。
藉由外交聯繫局的引介,我們飛到紐約拜會哥倫比亞大學的貝瑞教授(Professor Behre),他是陸軍部地理研究委員會的會長。後來,他把所有的昂貴儀器和裝備,都提供給赫門作科學測量。
接著,我們又飛往華盛頓,去見海軍水道測量機構的葛洛維上將(Admiral Glover)。這位性情很好的老船長,集合他所有的部屬,指著牆上的太平洋地圖,引見赫門和我:
「這兩個年輕人要來這裡查查地圖資料,你們幫幫他們!」
當一切漸漸有些進展之際,英國的盧姆斯丹上校(Colonel Lumsden)在華盛頓英國軍事大使館召開會議,討論我們未來的問題,以及順利成功的機率。我們獲得很多很好的忠告,還拿到一樣從英國空運過來、用來試驗木筏遠征的設備。英國醫官很熱情地提供給我們一種神秘的「鯊魚粉」,如果鯊魚太囂張,只要在水上灑一些這種粉,鯊魚就會立刻消失。
「長官,」我彬彬有禮地說:「我們可以完全依賴這種粉末嗎?」
「這個嘛,」這位英國人微笑地說:「我們也想知道這個答案。」
隨著出發的時間越來越近,我們的交通工具也從飛機變成火車、從雙腿變成汽車,於是荷包開始逐漸縮水,像個枯萎的標本。在買了飛回挪威的機票後,我們得到紐約找贊助人朋友,解決我們的財務問題。不料,我們卻在那裡碰到令人吃驚與灰心的問題:財務經理發燒臥病在床,他的兩名同事無權處理,必須等他回來上班才行。他們仍然很願意在財務上支持我們,但一時之間實在無能為力,所以要我們先延後計畫。然而,事情正進行得如火如荼,要我們突然停下來,根本沒有辦法。我們只能繼續下去,因為現在要煞車已經太晚了。我們的贊助人朋友同意解散這個聯合贊助的組織,好讓我們獨立而迅速地運作。
結果最後演變成我們手插口袋,在街上閒晃。
「十二月,一月,二月。」赫門說。
「還有三個月零幾天的時間,」我說:「但我們就是必須開始了。」
即使所有的事情都模糊,有一件事情我們卻絕對清楚:我們的航行是有目標的。我們可不是那些可以坐在空桶子裡從尼加拉瓜(Niagara)瀑布上面滾下來,或是坐在旗竿握柄上長達十七天之久的特技演員。
「沒有人支援口香糖和可口可樂。」赫門說。
在這一點上,我們深深地同意彼此的意見。
我們是可以得到一些挪威方面的資助,但那還是無法解決我們在大西洋這一邊的問題。我們可以申請補助,但這個有爭議的理論實在很難拿到補助金,而這正好就是我們必須進行這趟木筏之旅的原因:我們要讓這個理論不再具爭議性。然後,我們馬上發現,無論是新聞界、私人贊助者,或是所有的保險公司,都不敢把錢投注在這個他們認為是自殺之旅的活動;但是如果我們安全而且成功地歸來,則又另當別論。
一切看起來都沒什麼希望,有好幾天的時間我們甚至覺得好像在海上漂浮,沒辦法著陸。這時挪威軍事領事蒙堤卡斯上校出現了。
「孩子們,你們遇到問題了噢?」他說:「先給你們這張支票,等你們從南太平洋群島回來後再還我。」
其他還有一些人也如法炮製,很快地,我們獲得的私人借款已經措措有餘,不需要再仰賴任何團體的贊助。我們就要飛往南美洲,開始建造木筏了。
老秘魯人的木筏是由白塞木築成的,這種木頭在乾燥狀態下比軟木塞還輕。白塞樹只生長在秘魯,而且至少要安地斯(Andes)山脈那種高度的高山上才有,所以在印加時期,水手們會沿著海岸到厄瓜多,在太平洋海岸邊砍伐白塞樹,我們現在也打算這麼做。
當代的運輸問題已經跟印加時期不同了。我們有汽車、飛機,也可以找運輸局;但是,事情並沒有變得簡單一點,因為海關穿制服的保鑣永遠懷疑你的說詞,亂翻你的行李,如果你仍然幸運地入境了,他們就拿蓋印章這種型式來刁難你。我們真正害怕的,就是這些穿制服的人,因為他們有權決定不讓我們輕易地就帶著裝滿奇怪物品的大包小包,舉起帽子,彬彬有禮地用一口破西班牙語請求入境,然後再坐木筏離開,我們搞不好還會被關進牢裡。「不行,」赫門說:「我們一定要有官方介紹函。」
我有個很久沒在一起的死黨在聯合國擔任特派員,他開車載我們去那裡。當我們進入壯觀的會議廳時,一位黑髮的俄羅斯人正站在巨幅的世界地圖前演講,我們看到各國人員肩並肩地坐在長椅子上,安靜地聆聽,這樣的景況令我們嘆為觀止。
我們的特派員朋友,設法在休息時間找到秘魯的代表,之後又找了厄瓜多的代表。在接待廳柔軟的皮沙發上,他們津津有味地聆聽我們的航海計劃,知道我們橫越海洋是要證明在他們境內的古文明人,是第一批從他們自己的國度到達太平洋群島的人。兩位代表都承諾要通知他們的政府,並且保證當我們到達他們國家時,會給我們支援。崔佛•利埃(Trygve Lie)經過接待廳時,聽到我們是他的同胞,就走了過來,還有人建議他應該和我們一起上木筏航行,不過他在岸上所面臨的巨浪已經夠他應付的了。聯合國一位助理秘書,來自智利的班哲明•柯罕博士(Dr. Benjamin Cohen),他本身就是位著名的考古學家,因為和秘魯總統有私人交情,還幫我們寫了一封信給他。我們還在大廳遇到挪威大使——摩根斯提奈的威爾翰•范•穆瑟(Wilhelm von Munthe of Morgenstierne),從那時起,他就一直給予這趟遠征完全的支持。
於是我們買了兩張機票,飛往南美洲。當飛機的四個大渦輪開始一個接一個轉動時,我們癱坐在座椅上,精疲力竭。第一階段的行程已經完成,我們如釋重負的感覺難以筆墨形容。現在我們就要飛往探險之旅的出發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