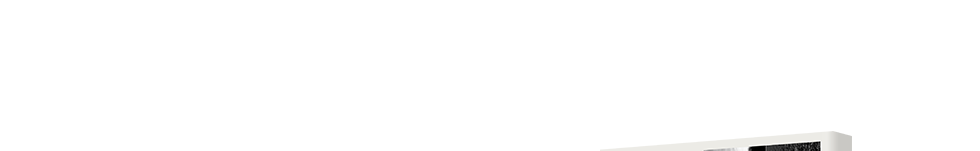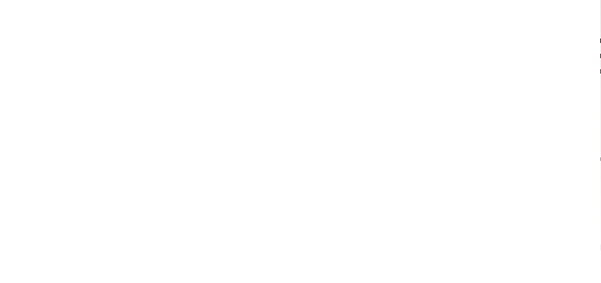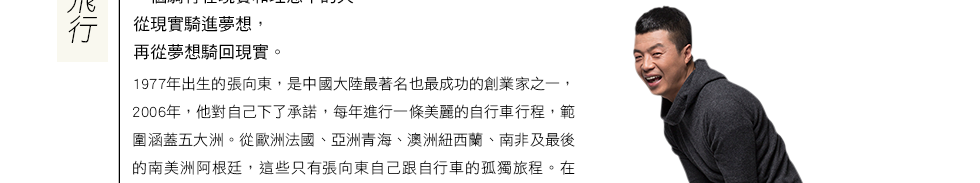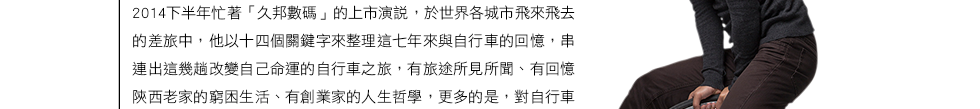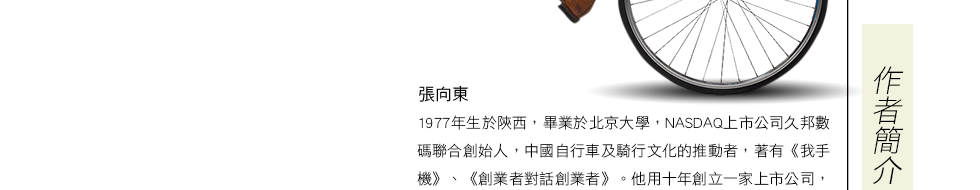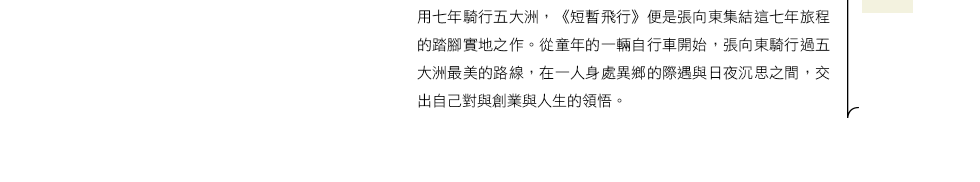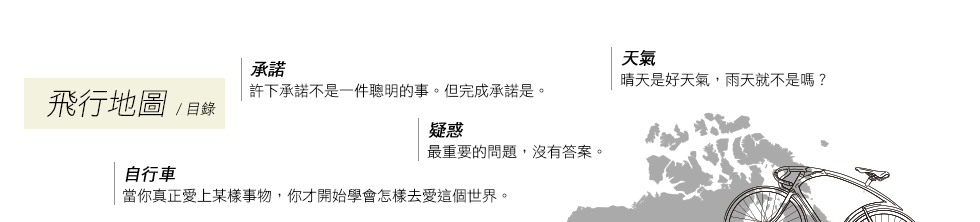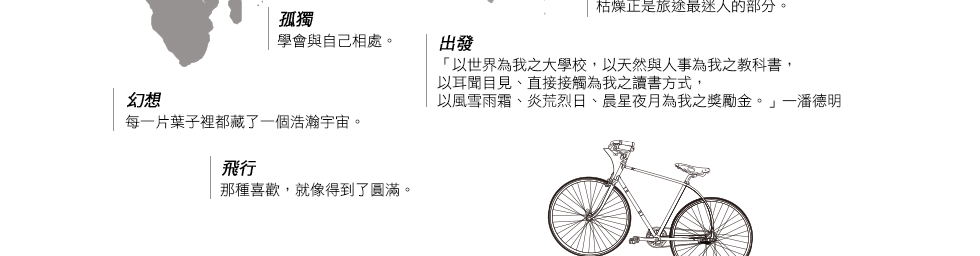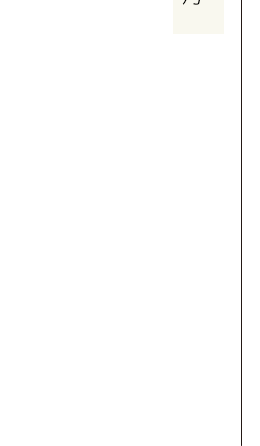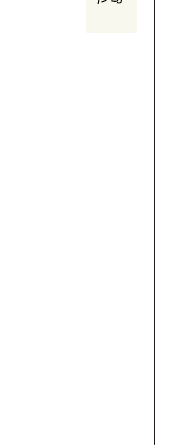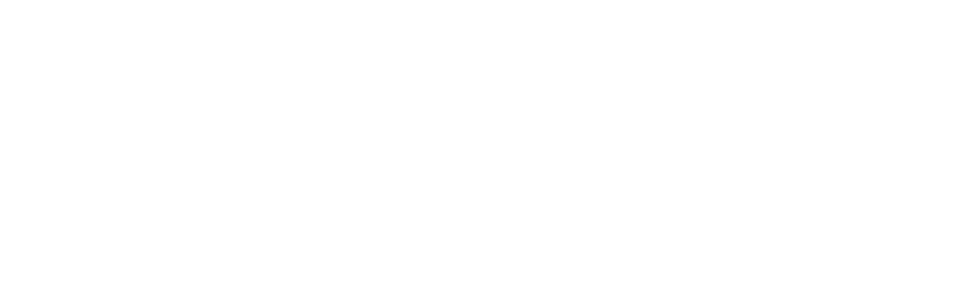天氣
晴天是好天氣,雨天就不是嗎?
看過一場話劇,叫《哥本哈根》。
故事講的是科學家海森堡和波爾的靈魂對話,用不同的角度,演繹發生在哥本哈根的歷史會面的各種可能。就是這兩個人,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,海森堡為德國研製原子彈,玻爾為美國研製原子彈。這兩個人在實驗室中的成就,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一九四○年以後的人類命運。
海森堡是否刻意讓德國的原子彈研製拖後?沒有人知道。坐在觀眾席的那天晚上,我好像剛剛發覺,自己作為地球上幾十億分之一,要在多少個幾百億、幾千億、幾萬億的轉捩點上不斷選擇,不斷幸運,才可安安穩穩地在那個時刻,坐在北京國家大劇院劇場第三排六號座位的位置上。
海森堡在物理學上,還有一個哲學高度的發現,那就是「不確定性原理」。物理專業的朋友用說給外行人的話給我解釋,說:「你無法測量一顆粒子的品質,因為你的測量已經改變了它。」我的第一反應是:「那現實世界沒有什麼可預測的可能,一切都是動態的,測不準的。」他說:「對。不確定性原理,曾經也被中國學界稱為測不準原理。」
在「第二次世界大戰」的尾聲,蘇軍占領柏林,海森堡一路逃亡,納粹員警四處追殺任何可能知道德國軍事祕密的人,海森堡是最重要的目標之一。就在員警掏出手槍,對準他腦門的那一刻,海森堡摸出自己最後的、唯一的財產—一包Lucky香菸,遞向員警,員警看了看,收起槍,拿走了菸,消失在夜幕中。
Lucky香菸,很多人叫它「好彩菸」。一包菸,換回了一個可能改變人類命運的人的生命。那還真的算海森堡好彩。
就是這個人的有意或無能,沒有為德國研製出原子彈,而波爾他們為美國研製成功了原子彈。美國人用原子彈轟炸了日本,日本宣布投降,「第二次世界大戰」結束,才有了我的父母,也才有了我,我順利長大,才有可能在世界各地騎行。那我也真算好彩。
而你看到這本書,這行字,真是巧到不能再巧。在此之前,人類歷史上任何一件大事是否發生,都會影響到我們是否以這樣的方式遇見。
如果從開天闢地、堯舜禹湯起追溯,歷史書裡的任何一件事在彼時彼處發生之前,都有無數個分岔口,如果算起來,所有事情發生的概率,原來都是那麼那麼那麼地小,小到無窮小。
不必追溯到那麼久遠,在每個人的命運裡,一件事情的發生,也經歷過無數個分岔口,同樣的,算起概率來,也都是那麼那麼那麼地小。
奇蹟是什麼?
奇蹟就是:它竟然就這樣!在那樣的時刻!以那樣的方式發生了!
它!竟!然!就!這!樣!
在!那!樣!的!時!刻!
以!那!樣!的!方!式!發!生!了!
命運就像一粒塵埃,時而停滯懸浮,時而盪來盪去,只是完全不能自行控制去向。
命運又像一隻螞蟻,在迷宮裡爬行,每遇一個路口,都猶豫難決,不知道每一次選擇的背後,會是什麼不同的結果。
想來,這個真相是多麼讓人絕望。一切都是夢中之夢,還有什麼力量去和命運決鬥。
有大概十多年的時間,我有嚴重的偏頭痛。每年有一個多月裡,每天會忽然發作一兩次,每次一個多小時。疼得死去活來,各式各樣的檢查和治療,都不見功效,疼了一個多月,倏忽一下,又完全沒事了。每當一年頭疼季開始,我就膽戰心驚。直到一天,遇見一個很有口碑的中醫。他說:「你的身體沒有任何問題,但有一點很重要—你要學會接受,接受自己,接受無常。」
教我學會接受的,是騎車。
那次是在法國,就在同一天裡,我遇到了騎行路上所有倒楣的事:迷路、斷鏈、下雨。
早晨出發時,天氣尚好。輕鬆快騎,二三十公里轉眼間就過去,路況不錯,只是轉上一條寬闊的公路後,身旁疾馳而過的汽車不斷朝我鳴笛。開始,我以為那是打招呼,法國人對長途騎車的人總是很友善,我也向司機揮手致意,後來才覺得有點不對勁,每個司機都邊按喇叭,邊揮手指向旁邊的輔路。我忽然醒悟:我騎上高速公路了。
大部分國家的高速公路是沒有收費站的,你不知道騎上的是什麼路,即使偶有標識法文的,我也看不懂。從巴黎出發前,朋友就告訴我,自行車騎上高速公路是違法的,要拘留。他還教我一招,說如果我不小心騎上去,遇見員警,不懂法文是優勢,還一定要裝作一點都不懂英文,那員警一般就會放你走人。
趁著呼嘯的警車還沒開過來抓人,我趕緊停下來,把車推下路基,轉上輔路。然後—你猜對了,很快,在法國發達的公路網上,我就不大確定自己到底騎在哪條路上了。偏偏這時候,開始下雨。
雨不算大,但每次打開地圖就不那麼方便了—要補充一句,那時候,手機的導航還不怎麼好用呢—岔路很多,我心神不寧地騎來繞去,到了一個不大的上坡,只聽「哢」的一聲,腳上立刻沒了阻力,回頭一看,只見斷了的車鏈像條死蛇,趴在坡中間。
我的修車技術實在乏善可陳,出發前才急匆匆地翻了翻說明書。一個高手懶洋洋地教給我幾個要點,他晃盪著扳手說,知道個大概就行了,荒郊野外的,車一壞,什麼都學會了,壞個七回八回的,水準就能趕上專業技師。
遠近看不到避雨的地方,只好埋頭鑽研說明書。雨水一會兒就打濕了紙。我站起來攔車,專門攔那些車上架了自行車的汽車。一輛旅行車停下,走下來一對夫婦,男的一看到躺在地上的車,就明白我的麻煩,可是他也沒搞明白怎麼把鏈條接起來。兩個滿手油污的人正相對無語地琢磨著,我忽然開竅,拿起工具,把鏈條連結處的軸頂了出來,套上新的,鏈條就接上了,順帶還為國爭了光—法國男人對我伸出大拇指:Chinese,So smart!
在有騎行文化傳統的國家,司機會主動問你是否需要幫助,但絕不會主動邀請你上車,那對騎行者來說,是不禮貌的,甚至是侮辱。我受了誇獎,更不好意思示弱,大概問了一下方向,揮手告別好心的夫婦,又騎了起來。雨中路線不明,不知道能不能在天黑前找到住處,我騎得心慌意亂,還胡亂擔心會不會被淋到感冒,會不會後續行程全部因病斷送。
雨越來越大,我已經連續走錯了好幾次,這次我打算,再遇到鎮子,就找個當地人畫地圖給我,好過再去看已經模糊不清的地圖冊。還沒找到小鎮,我看到草叢中一個穿了雨衣的獵人在訓練獵犬。我停下車,過去和他打招呼。只見他穿了件斗篷,叼著菸斗,慢悠悠地檢查著獵槍,幾隻獵犬在他的指令下,一會兒奔出去,一會兒叼根樹枝跑回來。
我走上前,沒先問路,而是先問了句:「下雨天您還打獵?」老獵人取下叼在嘴裡的菸斗,反問道:「晴天是好天氣,雨天就不是嗎?」
晴天是好天氣,雨天就不是嗎?
雨天算是好天氣的話,那下雪呢?下冰雹呢?刮著下坡也得猛踩腳蹬的逆風呢?
所有的天氣,都是旅途中不可預料的一部分,都是應該接受的風景的一部分。
也許是法國人有足夠的哲學傳統,一個獵人的隨口敷衍,都可以這麼有趣。我忘了那天最後是怎麼找到路的,只記得自己在雨裡慢悠悠地騎,還把所有關於下雨的歌唱了一遍,遇見野地的鴨子,就對牠們嘎嘎嘎;遇見乳牛,就朝牠們哞哞哞。
遠望風雪中的青海湖,是一大片凝固了的灰白。那灰白的一片,和落了雪的大塊平原不同,凝聚了磅(石簿)能量,以靜制動,隱而不發。風雪遮罩了其他聲響,我只聽到自己深重的喘息聲,呼出的氣息散在臉上,這是身體唯一感應到暖意的方式,任憑你發力猛踩腳蹬,也無法帶來一點暖流。
騎近水邊的時候,我卻發現青海湖並不平靜,湖水邊緣是結冰的,水面卻起伏不定,湖水發黑,聲響很大,讓人覺得不安。我在那樣的湖邊騎車時,總是盡可能地快騎,著急逃離,生怕有個怪獸爬出來一口把我連人帶車吞下去。
第二次帶隊去環青海湖騎行,四天四樣天。
一天晴,一天雨,一天風,最後一天雨後大放晴。
一開始我是和老天爺商量:「您看我們來騎車怪不容易的,您就刮一會兒,意思一下就停了吧。」老天爺沒完,我又邊騎邊說好話求他老人家:「真騎不動了,風把嘴巴封了,呼吸不了,好不容易遇見個下坡,還得踩,和上坡一樣累。行行好,別刮了吧?或者,反過來刮?」老天爺不理我!怒!最後幾十公里,一路罵,會罵的髒話用了幾十遍—心裡罵的,沒罵出聲,張嘴就給風憋回來了。刮大風那天,上午我們頂風騎了八十公里,隊友F臉色煞白,跌跌撞撞衝進飯館,連吃了兩大碗公麵條後,才緩過點勁來,有了力氣在餐桌上怒指蒼天無眼。
那是最艱難的一天,也最難忘。那年的環湖,隊友都記得特別清晰,所有的細節,都能一點一點逐步還原。付出最多的那次,總是得到最多的一次。就像……就像戀愛。
最後一天,開始還有雨,後來,藍天跟在我們車後,好像車後繫著一根長繩,扯著天幕,慢慢把滿天的烏雲扯了開來,藍天碧濤,是落幕的定格,站在路邊望向遠方,晚霞在草原盡頭染紅了天空,我們都不再說話。
大洋路(The Great Ocean Road)不長。從Warrnambool出發,到Geelong結束,只有三百多公里。
真巧 —一切都是那麼巧──和《哥本哈根》一樣,這段路也和世界大戰相關,是「第一次世界大戰」後,澳洲政府為了給退伍軍人安排就業所開發的專案。
公路沿印度洋而築,蜿蜒山中,乾淨、樸素,毫無花哨。從頭到尾,路況幾乎一模一樣的好。景色也是:山裡,是安靜的樹林;海裡,是洶湧的波濤;路,是一個坡又一個坡,一會兒上,一會兒下,不會非常大,就是沒完沒了。要想找點刺激驚喜,那是癡心妄想──哦,無尾熊是唯一的例外,牠們老老實實抱著樹枝睡覺,無論你怎麼叫牠喊牠,牠自巋然不動,兀自睡去。人世間的天荒地老、滄海桑田,於這樣的一個物種,只是大夢一場。後來知道,無尾熊的食物桉樹葉有麻醉功效,所以無尾熊才一直睡不醒。「大洋路、無尾熊,你不覺得都很像澳洲人嗎?簡單平淡。」一個澳洲朋友對我說。
我覺得這位朋友只說對了一半。大洋路上的天氣,可不簡單平淡。
每天早上,出門跨上車,抬眼一望,只見濃厚的雲層如得令箭,四散而去,那時總會心情舒展:「今天天氣不錯呀!」
不錯?
錯!
一進到山裡,大洋路上的天氣,像一個沒自信的情人,忽而暴虐,忽而溫柔,變幻頻繁,完全不可以按天來作為週期,只能以二十分鐘來計量。
剛下一個大坡,早晨溫暖起來的空氣忽然就變得涼颼颼,頭頂一大朵雲彩遮住了太陽,雨點兒就飄了起來,很快,烏雲密集起來,趕緊下車換上防雨的外套,才轉一個彎,又是陽光普照。好在剛才雨也不大,雨過去,天也不熱,只要拉開點防雨外套的排氣拉鍊就好。預料不到的是,再一轉彎,刮幾陣風,又開始下雨,好像老天在逗你玩。
連續兩天下午,老天爺還玩了一會兒惡作劇。雨點猛落幾下之後,瞬間變成了冰雹。花生米大的冰雹撒了下來,頭盔、車身被打得叮叮噹噹,倒熱鬧得很。自行車頭盔是防撞的,沒想到還有一天會用來遮擋冰雹。握著車把的手就沒那麼舒服了,雖然有手套,還是被打得生疼。大洋路上根本沒什麼遮擋處,停下、後退都是受罪,只能繼續往前騎,心裡祈禱:快點過去吧,快點過去吧。冰雹也真的就過去了,只一小會兒,就像舞臺換場景一樣,幕布一拉,天空就晴朗如洗,路邊牛群若無其事地在吃草,有幾頭還好奇地朝我哞哞叫。我很想問牠們,剛才下冰雹的時候,都躲在哪裡了?
我計劃出行的時候,都會查一下適當的季節;出發的時候,當然會查一下當地的天氣。每當那樣的時候,我就會想起那句話:
「晴天是好天氣,雨天就不是嗎?」
趨利避害,人之天性。
聰明和勞累,也都用在了「趨」與「避」上。但「趨」,即可得到嗎?「避」,即可逃脫嗎?想通這個道理,慢慢地我的旅行都不那麼計較了。天氣晴雨都可以,路況好壞都可以,國家發達落後都可以,都不錯,都前往。
前往阿根廷的時候,那裡正進入雨季。
可時間已經不多。
這一年我越來越忙,下半年整塊的旅行時間完全不可預料。我也不想把騎行五大洲最美路線的計劃再次延遲,我只剩下南美洲這最後一洲,就像一個鋼琴師彈起一支曲子,只剩最後一段音符,要他起身離席,真是折磨人。
簽證也不好處理,在那之前,我頻繁地出差,護照要連續辦理幾個國家的簽證,最後,這一次本該珍貴的旅行被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選擇:只有這段時間,只能是阿根廷。
從布宜諾斯艾利斯(Buenos Aires)飛往巴里洛切(San Carlors de Bariloche)的飛機上,空空蕩蕩,起飛時陽光燦爛,還沒落地舷窗上卻已經拉滿水線。走出機場,只見原野之上,雨霧連綿。雨季,像性格沉默的朋友,冷冷地看著我的到來。
那幾天的早上,吃過早餐,我就像在晴天一樣,坦然推出自行車,只多了一個程式是穿雨衣,然後,騎入雨霧之中。所以,阿根廷騎行的印象,第一是滿嘴的沙子。因為下雨,滿地泥沙,泥沙被前輪帶起來,剛好送進嘴巴裡。我只好一會兒把腦袋歪左邊,一會兒又歪右邊,但還是要不停地吐口水,一路呸呸呸。第二就是無邊無際的水汽,雨霧籠罩著湖面、樹林、山坡,還有前方的路,四野無人,如同夢中。有一日天氣大晴,放開速度,縱情狂騎,反而覺得不夠真實,不夠阿根廷,我甚至懷疑那天是否真實存在,是不是我在阿根廷某天晚上的一場夢。
當然,雨天會麻煩很多。衣服會濕,包要額外做防水,車會打滑危險,熱量消耗快。可是,山裡會幽靜,湖水會迷蒙,樹林會翠綠,風景會不同。你聽得到頭盔上的水滴下來,在你的思緒裡轟然作響,就像沉思者在地下溶洞中靜坐所聽到的那樣。
那天騎上山脊,雨勢稍停,前方岔路,一邊指向智利,一邊指向聖馬丁德洛斯安地斯(San Martin de Los Andes),這裡植物茂盛,又在雨水充足時節,每一樣都長得舒展大方。我見識淺薄,尤其在生物辨識上,只好說,那棵樹,那片草,卻叫不出名字來。南美生物,本來就和我熟悉的中國植被樣貌迥異,這樣一來,顯得更是神祕。時近傍晚,霧氣升騰,樹林很快融入其中,林海成了霧海,再遠一些,山谷的霧和山上的雲混沌一體。我想,也許世界開始的時候,就是這個樣子吧。
林中傳來幾聲鳥叫,鳥兒大概是餓了,在試探雨是不是真的要停,好出來覓食。鳥鳴在樹林迴響,山中越發顯得幽靜。這時,若是林中走出來一個山怪,或湖裡冒出一個水神,只需喚一下我的名字,微微向我招一招手,我一定棄車尾隨而去,從此遁世不出。
還有一次短途,是和幾個朋友在北京郊區。
也是雨天,但雨並不大,大的是霧,滿山滿谷的霧,像煙一樣,揮一下手,霧隨袖飄散。前後車距不到兩米,看不清人形,之前疏忽,都沒帶尾燈。有汽車小心翼翼地慢慢駛過,車燈全都打開,也要很近才可看到。路是上坡,騎友一起喊著一、二、三、四,節奏一致,踩踏往前。心裡暗自慶幸:不是大下坡,否則更危險。
心裡只顧提防大霧的危險,更看不到坡的高度,踏頻慢而穩定,反而很容易騎至山頂,汗水浸透了騎行服,大家坐下來喝水。山風吹來,霧徐徐散去。我們一起發現,原來國畫山水如此寫實,水墨就是霧散後的山色。
待霧如收網一樣,攏往山後,我們騎上車,如滑翔的鳥兒,急遽沿公路而下。要是山下看得到,一定以為我們從雲中飛來。
我還沒有在冰雪之上騎行過呢。那應該要寬闊防滑的輪胎,防結冰的雪鏡,保暖防水的騎行服,手套也得特製,又保暖又靈活。然後,在一望無垠的雪國,慢慢前行,要是雪厚,有時候還得推行吧?下坡時候,一定會翻很多次車,摔很多跟頭,也可能一下人車兩路,「短暫飛行」,爬起來就已經鼻青臉腫了。我想,那一定很有意思,一定有很多樂趣,是現在的我無法想像的樂趣。
在出發之前,有一些事情是可以想像的。比如:會有天氣變化,會累,會看到很美的山和水。
但更多是無法想像的。
比如當一大朵雲彩移過來,把影子投射在剛好停下來的你的身上,那時候海正平和,深藍不語。再比如,霧正納入深谷,你有點餓了,邊騎邊看測速器上的數字,估計到達的時間。再比如,雨忽然大了起來,你無處可躲,倉皇中停在一棵樹下,明明是下午,天卻黑了,閃電在遠處無聲地劃了一下,你還在想要不要衝出去繼續騎,劈啪一聲,雷就在耳邊炸了,心裡好慌。
多巧啊,那些時刻,你就恰好在那個國家那條路上的那個地方,見過那樣的風景。
再也不會被重複,再也不會被任何人重複。
想到這一點,每次出發,我就覺得路上遇見的一切,都是我期待發生的部分。 |